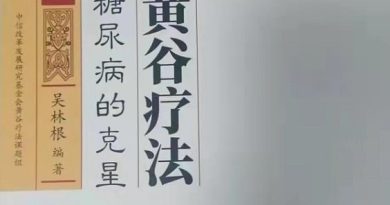冯志强(Joanathan Fon):ChatGPT 谈文学讲父爱——朱自清《背影》与冯志强《父亲的目光落在我的背上》对读
以下是ChatGPT 撰写的一篇对于文学作品剖析评论的文章。出于好奇便给予发表。诸君不妨阅读并且体味人工智慧如何体察人类情感表达和评介人类的伦理关系。文末附录了这两篇文章的全文,供读者自己体味一下人工智慧有多少程度理解人类智慧。
ChatGPT
在中国现代散文的长河中,朱自清的《背影》以其深沉含蓄的笔触,描绘出一位父亲无言而厚重的爱。而在当代海外华人的书写中,冯志强所著《父亲的目光落在我的背上》以跨代移民的眼光重温父子之情,延续并发展了“父爱如山”的文化主题。两篇散文以“背影”为核心意象,通过目送的姿态和沉默的表达,共同展现出父子之间那份隐忍、深刻又绵长的情感纽带。
2016年6月,父亲节期间,定居多伦多的冯志强写出了《父亲的目光落在我背上》,虽然年纪已达七旬,依旧嘘嘘道出游子情,父亲情,甚至祖辈的亲情。将时空错落的这两篇纪念父爱的散文放在一起温读,可以读出什么样的效果呢。
一、从“背影”到“目光”:隐形的父爱延续
朱自清在《背影》中写下:“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这一幅跨越月台买橘送子的背影,是中国无数读者心中最具力量的父亲形象之一。背影本身不言不语,却承载着千钧的父爱与牺牲。
而冯氏的《父亲的目光落在我的背上》则写道:“我感觉父亲的目光落在我的背上,我知道的!”这是一种被注视的感知,是作者在走异国他乡,离别时的情绪高峰。不同于朱自清的“看到”父亲的背影,这里是“被看到”——目光在背后,父亲无言,儿子却心知。这种移民别离中的凝视,让“背影”不再是视觉上的终点,而成为心灵流落的记忆长明灯。父爱永远在肃穆中孤立。
二、时代与身份:两个“父亲”的不同处境
《背影》诞生于1920年代,彼时中国正处于民国初年的动乱中。朱自清的父亲,是一个中产家庭中努力支撑生计、默默奉献的典型代表;儿子初为青年,初出茅庐,尚未理解父亲的劳苦。当“父亲吃力地爬上月台”这一幕出现,情感骤然升华,成为成年子女对父爱的第一次深刻体会。
而《父亲的目光落在我的背上》则是在移民加拿大多年后的回望,作者出国时已年逾中年,既是儿子,也是父亲,写成此文时甚至荣登祖父。他说:“我是父亲,我有责任为自己的儿子创造条件。”这种自觉将父爱的传承推向三代对话,不只是怀念,更是对“父职”的理解和延续。这种跨代反思,是当代移民叙事中的显著特征。
三、文学风格与情感表达:从含蓄到直白,从内敛到升华
朱自清以精练细腻的文笔,描绘了一个典型的“沉默父亲”,情感内敛克制。文中数次提到“我眼泪又来了”,却始终未有直接抒情,而是通过动作、场景、话语间的空白,展现情感的深沉。
《父亲的目光落在我的背上》则更具现代散文的自由表达特征。作者直接写道:“爸爸,我对不起你。儿子不孝,没法陪你走到最后。”更写道:“儿子,父亲对得起你!”这种情感的外放,既是一种文化差异(中西表达方式的融合),也是一种自我角色确认的宣言。正是这种从含蓄到坦白的演变,标志着时代的变迁和价值观的演化。
四、物件与场景的象征意义
朱自清文中“橘子”作为象征,代表父亲在艰难生活中的温情;而冯氏作品中“新英汉字典”则是一位父亲的象征性赠别。两件物品虽微不足道,却各自承载了巨大的情感容量——一个是旧时代父亲给儿子的营养与照顾,一个是新时代父亲对儿子学习与发展的祝福。
场景上,《背影》的月台与《父亲的目光落在我的背上》的上海弄堂口,分别成为父子告别的舞台:一个是车站的匆匆背影,一个是走异国他乡的永久分别。这种空间与命运的变化,也体现了现代人生活路径的分化与全球化背景下家庭结构的转型。
五、结语:父爱在时间与空间中延续
无论是在民国初年的北平月台,还是在世纪之交的上海弄堂口,父爱都在静默中传递;无论是橘子还是字典,都是父亲交托给儿子的生命信物;无论是朱自清的“泪湿眼眶”,还是海外父亲的“流泪书写”,他们都共同发出一声跨越年代的心声:“我懂事了,我已成为了你!”
《背影》让我们懂得父亲的沉默背后是无尽的爱,而《父亲的目光落在我的背上》则告诉我们,只有经历父亲的角色,才真正体会那份离别与传承的重量。这种来自父亲、穿越子女、流向未来的情感,是中华文化中最朴素、也最伟大的情感之一。
附一:
朱自清作于1925年的《背影》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然后他颠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作者简介:朱自清(1898—1948),现代散文家、学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江苏扬州人。他的散文,结构严谨,笔触细致,不论写景抒情,均能通过细密观察或深入体味,委婉地表现出对自然景色的内心感受。抒发自己的真挚感情,具有浓厚的诗情画意。主要作品有《毁灭》《踪迹》《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等。
附二:
冯志强作于2016年月6月18日父亲节的《父亲的目光落在我的背上》

父亲节写父亲。我也写一篇吧。父亲在1994年离开我们而去。近年来,每年返家探望母亲,都会去他长眠的地方,行礼。我呢,自己做父亲有三十二个年头。儿子也当了父亲,不过,才两年不到。
父亲挺为我感到骄傲的。实实在在的高中课程才学了一年,1966年,全中国的学校都停课了。高一第一学期的成绩单出来时,各科成绩几乎满分,有几科的考试卷子增设附加题,考分都超过满分。父亲在春节时分,逢人便要将那份成绩单拿到人前显耀一番。这时,我感觉父亲并非深不可测,也有钟爱儿子的亲情。
至今,即便行笔的此时此刻,我就记得两件事。
父亲陪我背乘法口诀。男孩小时候,上学真的不上心。背乘法口诀,父亲督查几次,就是背不下来。一天晚饭后,父亲便叫了我出去走路,就在出了家门的马路上,他一口一口让我跟着他学说,走着跟着说,竟然就背完整了。
还有,男孩小时候,学坏都不知道。小学两年级时,我偷偷摸摸学抽烟,大前门两毛九分一包,飞马牌两毛两分一包吧。我买了大前门抽,被帮佣,替我们家做家务做菜的老妈妈发现了。 她必定告诉了父亲。那天,父亲也叫我出去走路,问我抽烟的钱哪里来的。
我告诉他,钱是从零花钱里积下来的。那时候,我和妹妹们,每天都会得到五分钱买点心吃的。五分钱可以买甜大饼,三分钱买葱油大饼。有时候,祖父祖母也会给出一毛几分。我积下钱,买了大前门偷着吸。父亲告诉我,要用钱,可不能拿别人的钱。讲明原因,可以问大人要的。
接着,他问我:“你爸爸抽烟吗?”他自己答了,“也抽过,但是戒了。那对健康有坏处。”他随随便便地说下去:“你把它扔了吧。”於是,父亲转换话题,讲一些路边店铺的来历。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祖父是大家长,在上海老城厢豫园墙外安仁街已经几代居住下来,父亲的曾祖父就已经是当地的人物了。
从此,我不再抽烟。后来,我长大了,离开父母,插队落户到农村,又下煤矿,再次染上抽烟习惯。做了父亲,回到父亲身边,还在抽烟。对此,父亲可没有多说一句。不过,现在,我早已不抽了。儿子在身边成长。他刚去中学上课时,回来同我讲,同学说他吸毒,因为他身上有烟味。我知道了,烟就戒了,一直到现在。
父亲真的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我们最后一次双目对视,记得是1992年5月26日。那是在弄堂口为我送别。因为这次我来加拿大,说实话,也不知道确实日期回去,所以太太儿子和妹妹们都送我去机场。妈妈则陪我走到弄堂口。父亲健康不如以往,不常出家门。
我和太太儿子与妹妹们在弄堂口准备上车走了,却听到父亲在背后招呼我的名字。他步履散乱,却招呼我的名字很急,手里举起一本书。那是《新英汉字典》,增补版。我有意将它留在家里不带走的。我接过来,心里有点不耐烦,还是收在背包里。他神色颠颠,眼光笔直看着我。我们心照不宣,都明白,也不明白,再相见时将在何时何地。我心里好闷。
我知道父亲心里难受,但是不知道父亲心里如何地难受!他是老派人,喜欢儿女围在身边,有儿孙就心满意足。可是儿子走了!我不敢逗留更长时间,转身上车,眼睛就不敢转过去,多看一眼父亲。可是,我感觉父亲的眼光落在我的背上。我知道的!
至今,我一直在心里自责:爸爸,我对不起你。儿子不孝,没法陪你走到最后。但是,老天啊。我也是父亲,我有责任为自己的儿子创造条件,让他有好的发展。离乡背井图什麽?给儿子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在自由平等的环境里实现自己的人生。现在,我要对儿子发声:儿子,父亲对得起你!可怜天下父母心吧。(我是流着泪,不断暗暗喊着“爸爸”两字,写下这最后几行字。)
作者介绍

冯志强(Jonathan Fon),加拿大华人,定居多伦多。跨族裔媒体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
1986年至1989年,在上海《中国合作经济报》担任国际版记者、编辑;同时受聘为国际合作社联盟机关刊物《国际合作评论》季刊撰稿报道中国供销合作社动态和介绍刘少奇合作社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发展。
1992年开始,先后在多伦多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国语广角镜》、《Omni 2 国语电视》、城市电视《家国纵横》等电视台时评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热线》的长期特邀嘉宾;时评言论在各种印刷或电子媒体发表,如美国的《华夏文摘》等。同时接受英语电台、电视台和报纸的采访,受邀点评时事。
出版时政评论文集《横看成岭竖成峰》和散文集《人生五味瓶,人生五色版》。
2022年担任加拿大《健康生活报道》专栏作家、加拿大中文记者联合会(Canadian Federation of Chinese Journalists)、加拿大中文记者和编辑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Journalist and Editors)等专业媒体协会法律顾问。
法律服务专攻移民、难民聆讯和上诉,房东房客纠纷和小额债务等法庭诉讼;也提供国际文件认证公正法律服务。
2021年多伦多市26选区市议员候选人。